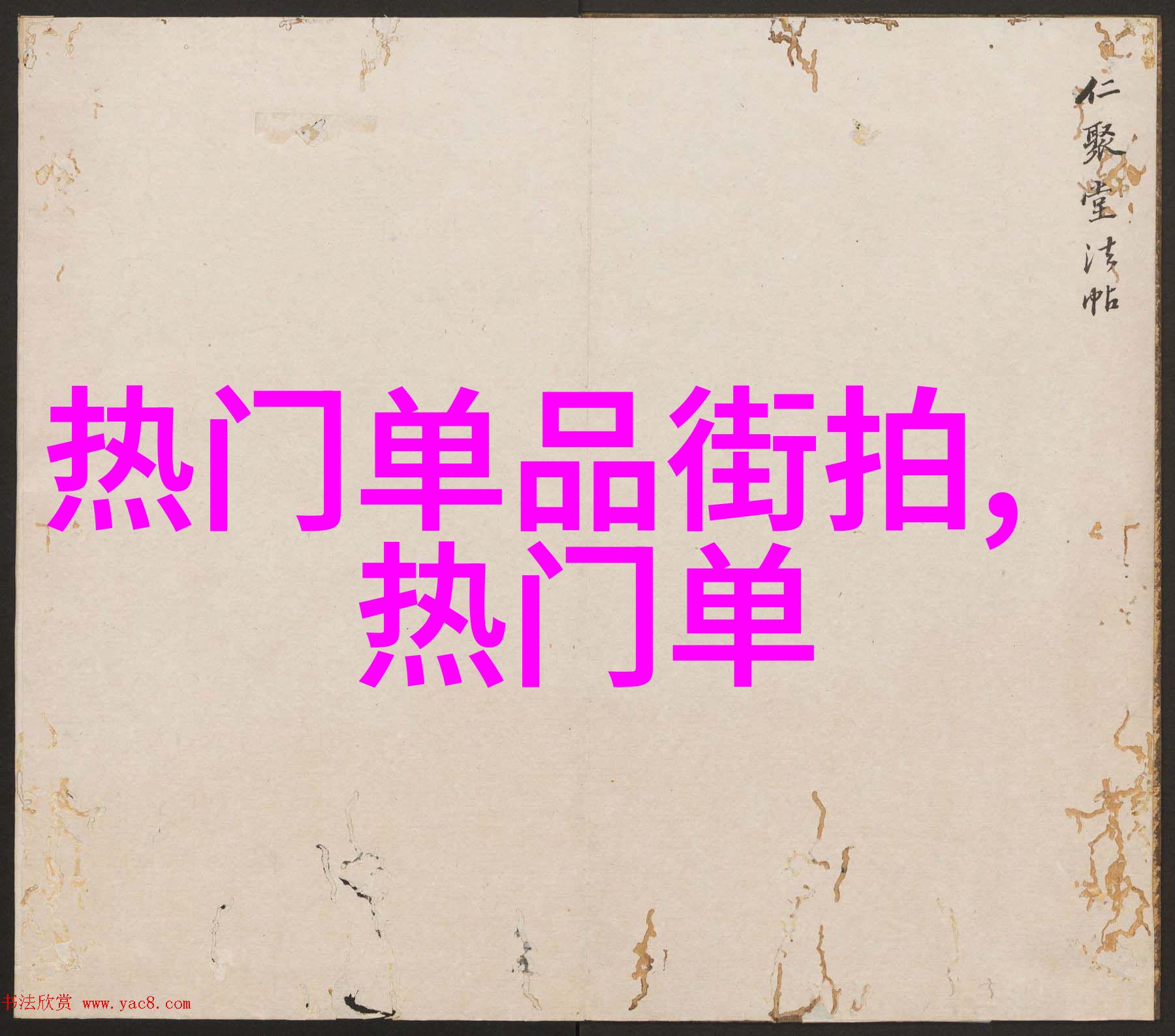《芭比》以女性尤其是年轻姑娘为绝对主角,用一场盛大的游戏搭建起取悦女孩的糖果屋。
《芭比》上映第一天,中国市场的排片比例是2%,当天,华纳公司社交账号下的评论大多是“看不到”。第一个周末过后,电影院不能无视《芭比》的高上座率,谨慎地增加了场次,到周一时,它的排片比例上升到8.7%。这是一部以女性尤其是年轻姑娘为绝对主角,目标观众也以年轻姑娘为主的电影,它在市场上的“被低估”颇值得玩味。
围绕着《芭比》的拍摄和公映,最有戏剧性的一个段子发生在导演格蕾塔·葛韦格和女主角兼制片人的玛格特·罗比谈节目时。她俩透露:如果剧本里存在一两处涉及性别议题的争议点,华纳片厂的高层们一定会要求修改;索性剧本里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性别议题的争议点,高层们只能答应主创班底:先拍着看看吧。结果,就是这样“拍着看看”地拍完了。
可《芭比》何曾制造一个充满攻击力和挑战感的、大杀四方的“大女主”?这根本是一部温和、俏皮、皆大欢喜的“小甜水”电影,是一场从开始到结束都发生在玩具屋的女孩们的过家家,整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取悦老老少少的女观众的一座豪华芭比屋。
电影当然和现实发生了交集。电影里的芭比和肯初来乍到人类真实世界,他们登陆马里布海滩,帅气的肯得到他在芭比乐园里未曾享受过的关注,而芭比成了男性凝视下的“人形玩偶”。这和现实中的拍摄现场重合了:围观群众认出了两位主演,路人们纷纷和扮演肯的高斯林打招呼,赞美他的个性和行头“酷帅”,对衣着清凉的罗比,则上上下下地打量。
又何止罗比和芭比的海滩遭遇重合。这场事先张扬的过家家,多少现实照进了游戏。所以并不奇怪,那么多素昧平生的女观众在电影院里爆发了惺惺相惜的大笑。《芭比》密布的荒唐笑点,来自多少女性在日常中被忽视、被误解的真实感受:为什么女孩走在街头被异性尾随会感到不安?为什么路人看来毫不在意的“玩笑”,会让姑娘感到被冒犯并为此暴怒?为什么女性的焦虑和痛苦需要不断地向外界解释,尽管如此仍未必被接受和理解?
两种性别的生理差异是无法回避的,不同性别对世界的感知成了分道扬镳的两种路径。“经典芭比”离开乐园,是因为她心底产生了恐惧和哀伤,《芭比》放肆的笑声中深藏着眼泪的暗影,表现在初来乍到繁华大都会的肯和芭比——肯满眼看到光鲜灿烂的“征服”和“成就”,他天然地接受了“一切尽在掌握”这样的信念;而芭比呢,她朦胧地感知到女儿和母亲之间、少女和中年少女之间因为误会产生的隔阂,这隔阂的痛苦是清晰的,她触目所及是叹息、黯然神伤,以及隐秘的悲伤与泪水,她看到男孩一样会陷入孤独无助,她看到不可逆的年华老去……肯兴冲冲地抛下芭比,单身返程,野心勃勃地要把“乐园”改造成“王国”。芭比却流着泪对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说:“你真美啊。”华纳片厂一度觉得芭比和老太太交谈的镜头是多余的,导演据理力争才留下这个片刻。
葛韦格在创作《芭比》的剧本时,她赞美了女性“爱与平和”的气质,也没有回避她们天性中的弱点。“自我实现”是逆水行舟的童话,相比之下,“成为附庸”的太大了,女孩们并不知道看起来轻易的人生被命运暗中标注了什么样的代价。肯轻而易举地把“芭比乐园”颠覆成“肯的王国”,“古怪芭比”大叫:“这简直就像白人把天花带到美洲,原住民可没有抗体啊!”这个酸涩的“玩笑”,何不是暗暗地呼应着波伏娃振聋发聩的名言:“女人的不幸在于她受到不可抗拒的包围,她被告知但凡听之任之地滑落人生,就会抵达极乐天堂;当她发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,为时已晚,她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。”
“芭比们”的堕落是群体性的,重新唤醒她们,却要一个一个地团结、争取,这简直构成清醒又沉重的寓言。诚然,《芭比》全片是一则粗线条的寓言,热爱芭比的中年少女闯入乐园,为了让芭比们重拾自我意识,接连“强势输出”。对电影心存不满的观众会非议,这个高光段落是脱口秀式的金句集合,是宛如儿戏的情绪煽动的胜利。但这样式简笔画的剧作,刚好和塑料感极强的芭比娃娃屋相得益彰:这就是游戏,这就是过家家。导演葛韦格的才华,不仅表现在她让网络段子、现实感受和歌舞片的视听达成和谐的三重奏效果,更重要的在于,她面对“芭比进入现实”这个命题作文,反向操作,用彻底的解构完成虚构。
葛韦格在采访中袒露了她少女时期的秘密,她到13岁时仍独自玩洋娃娃,而这种行为遭到家长和同学的唾弃。在《芭比》的创作中,她坚定地实践着那个她私藏多年的秘密想法:上了年纪的姑娘怎么就不能玩洋娃娃了?并不一定要小女孩摆脱洋娃娃的幻梦,而可以颠倒过来,大姑娘在洋娃娃的过家家里,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在电影出字幕之前,葛韦格戏仿了《太空漫游2001》的经典开场,小女孩们得到芭比,就像类人猿学会使用工具,拉开文明的序幕。这种女性文化的“构建”很快被证明是封闭的谎言,虚妄的游戏被糟糕的现实解构,但是现实照进游戏也无妨,吸纳了现实的失望、创伤和狼藉,还能重建一座新的女孩乐园——解构的尽头是全新的虚构。
《芭比》用一场盛大的游戏搭建起取悦女孩的糖果屋,它仍然是假的,人造的,可是,像这样为了女孩、献给女孩、和女孩在一起的“糖果屋”,在电影院里不是太多、而是太少了。